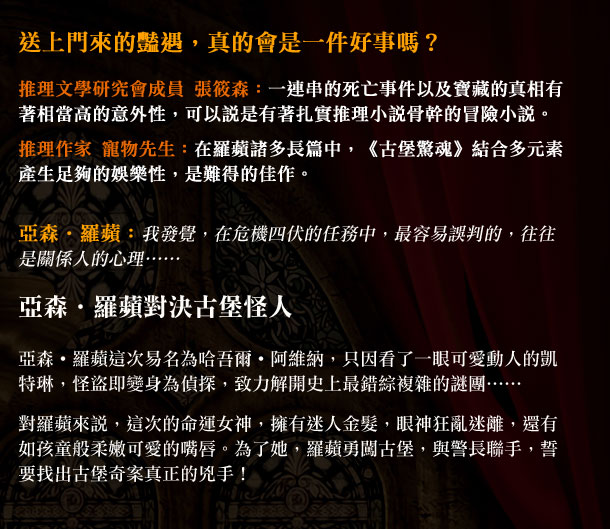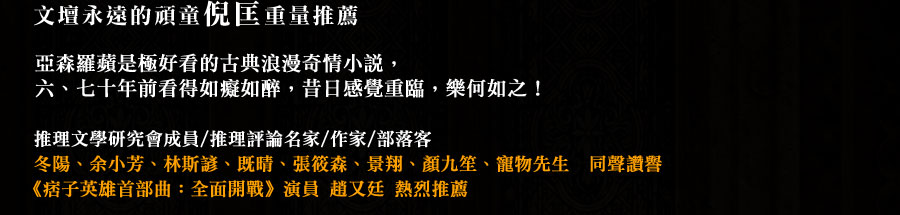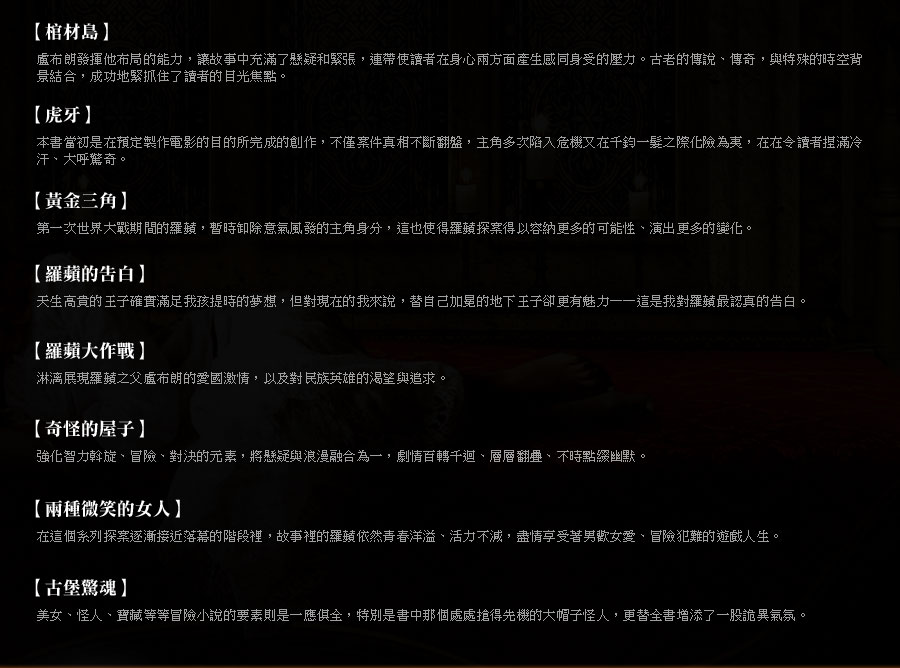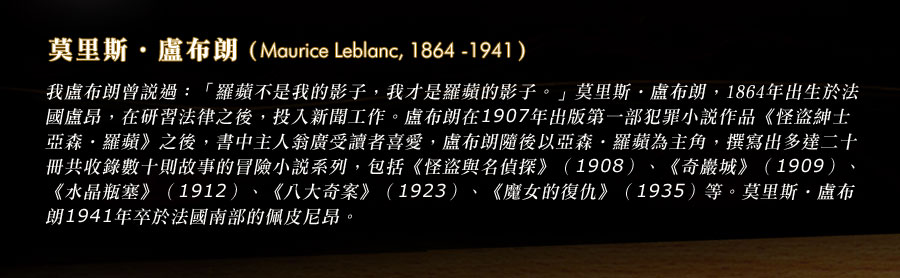|
燈光下,阿維納得以恣意欣賞這副風景,女子一頭金色捲髮圈起姣好的臉龐,她身材高挑,苗條纖細,玲瓏有致,穿著一件剪裁略顯過時的洋裝。
哈吾爾.阿維納原本就魅力無窮,女人緣極佳,所以他想自己大概又走了什麼好運,打算像平常一般,接受這天下掉下來的豔遇。
「我應該不認識您吧,夫人?」他露出微笑,「我們沒見過面吧?」
對方打了個手勢,意思是他說得沒錯。於是他接著說: 「敢問您怎麼有辦法進來呢?」
女子拿出一把鑰匙,他見了驚呼出聲:「原來您有我家鑰匙!這也未免太有趣了。」
他越來越相信,一定是自己不曉得在哪兒吸引到這位美麗的訪客,而輕易上勾的她,抵不住內心莫名的慾望,才會自動找上門來,準備投懷送抱。
於是他走近女子,如往常般自信滿滿,決心不放過這誘人的機會。然而,出乎意料地,年輕女士卻往後退,伸直了雙手阻擋,滿臉驚恐喊道:「別過來,不准靠近我!您不該這樣…」
對方慌張的模樣令阿維納一陣錯愕,接著,女子竟又哭又笑,她渾身顫抖,非常激動,阿維納不得不好言安慰:「拜託您冷靜點,我不會傷害您的。您又不是小偷闖空門,應該也不會對我開槍吧?所以,我怎麼可能傷害您呢?好了,您不妨說說來意吧!」
女子試圖恢復鎮定,她喃喃說著:「我想向您求救。」
「但我的工作並不是救人啊!」
「看起來是…只要您願意,一定辦得到的。」
「唉呀!您真是太抬舉我了,那麼,假如我想擁您入懷也辦得到囉?您想想,當一位女士在午夜時分,來到一位男士家,又生得像您這般花容月貌,窈窕動人…若我因此起了遐想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吧?」
阿維納再度靠近女子,這回對方不再抗拒,他將女子的手握在掌心,輕撫她的手腕及裸露的手臂,他突然覺得,如果現在將女子攬入懷中,她應該不會推開自己,畢竟她現在情緒十分脆弱。
於是,微醺的阿維納伸手輕輕摟住女子的纖腰,正想擁抱她時,卻望見一雙驚恐的雙眸,楚楚可憐的小臉上寫滿了憂心與哀求。因此,他停下動作,開口致歉:「請您原諒,夫人。」
對方低聲回答:「不,我不是夫人,我還是小姐。」
然後她接著說:「我了解,我在這種時間,有這樣的舉動,也難怪您會有非份之想。」
「啊!絕對有非份之想的,」他戲謔地說,「一到午夜,我對女人的感覺就脫了序,甚至會想些荒唐事,害我變得魯莽無禮,我得再次跟您說抱歉,是我不好,這樣可以嗎?您不會再生我氣了吧?」
「不會。」她回答。
阿維納嘆了口氣:「老天,您真是秀色可餐,結果您來這兒的原因卻跟我想得天差地遠,太可惜了!所以,您是像許多人去倫敦貝克街找福爾摩斯一樣,專程來這兒找我指點迷津的嗎?既然如此,小姐,麻煩告訴我事情原委,盡可能說明清楚,我會全力以赴,那麼,就洗耳恭聽了。」
哈吾爾請女子坐下,儘管他愉快、體貼、誠懇的態度已讓對方安心不少,但女子依舊臉色蒼白,如孩童嘴唇般鮮嫩的雙唇,美得像幅畫,卻老是緊緊抿著,只是眼神中已多了信賴。
「很抱歉,」她聲音帶著顫抖,「或許我說不出個所以然,但我真的覺得不對勁,有些事情……很怪……讓人想不通,我總覺得會出事,心裡很害怕……沒錯,我已經覺得害怕了,我不曉得自己在怕什麼,畢竟也無法斷定一定會出事。喔!天啊!太可怕了……我好痛苦!」
她的手撐著前額,似乎想驅散讓她筋疲力盡的念頭,看來十分疲憊。哈吾爾見她如此恐懼,心中頗為同情,為了緩和她的情緒,哈吾爾笑著說:「您看起來好緊張!別這樣,緊張也於事無補。打起精神來,小姐!依我看,從您來找我幫忙那一刻起,就沒什麼好怕了。您是從外省來的嗎?」
「是的。我早上從家裡出發,抵達時已經傍晚了,我很快找了輛車趕來這兒。門房告訴我您的門號,他以為您在家。我按了門鈴,卻沒人應門。」
「沒錯,傭人都請假,我則去餐廳吃晚餐。」
「所以,」她說,「我才會用這副鑰匙開門…」
「誰給您鑰匙的?」
「沒人給我,是我偷來的。」
「從誰那兒偷的?」
「這我待會兒再提。」
「別讓我等太久,」他說,「我等不及想知道了!不過,先等一下,小姐,我打包票您從早到現在都沒吃東西吧?您大概餓扁了!」
「不會,我在這張桌子上找到一些巧克力。」
「太好了!但是除了巧克力還有別的食物,我先弄點給您吃,然後再好好聊聊,您覺得怎麼樣?坦白說,您真年輕,有張童顏般的臉孔!我竟然把您當太太看!」
他笑容滿面,試著逗女子開心,接著打開餐櫥,拿出一些餅乾及甜酒。
「您叫什麼名字?我總得知道您的名字吧?」
「等一下,我會一五一十告訴您的。」
「好吧!反正不需要知道您的名字也能弄東西給您吃,來點果醬嗎?還是蜂蜜?當然,您美麗的朱唇必定喜歡蜂蜜,廚房裡有上等蜂蜜,我這就去拿。」
哈吾爾剛走出書房,便聽到電話響。
「奇怪,」他嘀咕著,「這時候會是誰打來?小姐,我接個電話。」
他接起電話,稍微調整一下語調:「喂?喂?」
話筒那頭傳來聲音,感覺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:「是你嗎?」
「是我。」他回答。
「算我走運!」那個聲音說道,「我找你一整天了。」
「真是抱歉,親愛的朋友,我去了劇院。」
「所以你現在回來了?」
「是這樣沒錯。」
「很高興能跟你通上電話。」
「我也是。」哈吾爾答道,「不過你能回答我一個問題嗎?我的老朋友,一個小問題?」
「有話快問。」
「你究竟是哪位?」
「什麼?你不記得我了?」
「恐怕是的,老朋友,到現在都想不起來。」
「我是貝舒,戴歐多赫.貝舒。」
哈吾爾.阿維納不動聲色,說道:「不認識。」
話筒那端的聲音提出抗議:「怎麼會不認識!當警察那個貝舒啊!貝舒,保安局警長。」
「喔!我聽過你的大名,但還沒榮幸與你結識...」
「你開什麼玩笑!我們不曉得合作幾次了!像那個『百家樂賭局』、『金牙男』,還有『十二張股票』?這幾個案子辦得可真漂亮,我們一起破案的啊!」
「你應該搞錯了,你確定知道自己在跟誰講電話嗎?」
「當然是跟你囉!」
「我是誰?」
「哈吾爾.阿維納子爵。」
「這是我名字沒錯,但我可以保證哈吾爾.阿維納不認識你。」
「或許吧!假如哈吾爾.阿維納換個名字應該就認識我了。」
「呦!說來聽聽。」
「比方說,換成『巴內特偵探事務所』的吉姆.巴內特,或是偵破『奇怪的屋子』一案的約翰.艾納里。還需要我說出你的真名嗎?」
「請說,別以為我會不好意思。」
「亞森.羅蘋。」
「很好!你說對了,那就沒什麼好隱瞞了。沒錯,這算是我最眾所皆知的稱號。所以,我的老朋友,有何貴幹?」
「我需要你幫忙,快來吧!」
「你也會需要我幫忙?」
「什麼意思?」
「沒事,我很樂意供候差遣。你在哪兒?」
「勒阿弗爾。」
「去那兒做什麼?你做棉花買賣嗎?」
「不,是為了打電話給你。」
「這可真妙,你離開巴黎跑到勒阿弗爾,就為了給我打電話?」
哈吾爾提到這座城市名字時,年輕女孩突然顯得惴惴不安,她自顧自地說:「勒阿弗爾?有人從勒阿弗爾打電話給您?真奇怪,是誰打來的?讓我聽聽。」
不等哈吾爾同意,女孩已經抓起分機話筒,同哈吾爾一起聽著貝舒說話:「不是啦!之前我人在鄉下,那裡沒有夜間電話可用,我才找車子載我到勒阿弗爾,現在我要回家了。」
「所以呢?」阿維納問。
「你知道哈迪卡提爾港嗎?」
「當然!位於塞納河中央的沙洲,離河口不遠。」
「沒錯,就在利里博恩港及唐卡維爾港之間,離勒阿弗爾港三十公里遠。」
「你想我會不知道嗎?我在塞納河三角洲和諾曼地科區長大的,這些地方我瞭若指掌。所以你現在是睡在沙堆上嗎?」
「你在胡扯什麼?」
「我說你現在住沙洲那兒嗎?」
「住沙洲對面,這兒有一座可愛的小村莊,名字就叫哈迪卡提爾,我在這兒租了幾個月的房子,想好好休息,是一棟茅草屋別墅...」
「跟心上人一起啊?」
「沒有,不過我倒是替你保留了一間客房。」
「你什麼時候變這麼貼心了?」
「有件事頗為錯綜離奇,我想找你幫忙釐清。」
「因為你自己解決不了嗎,胖兄?」
哈吾爾注意到年輕女孩越來越焦慮,又開始激動起來,他原本想拿走她手裡的話筒,但女子緊抓不放,貝舒又強調:「情況緊急,事情已經很麻煩了,結果今天,這邊又有位年輕女孩失蹤...」
「失蹤這種事常有,不需要大驚小怪吧!」
「不,不只失蹤這麼單純,其中有些細節很叫人擔心,而且...」
「而且什麼?」哈吾爾不耐煩地嚷著。
「就是下午兩點的時候,發生一起兇殺案。那名失蹤女孩的姊夫沿著公園河岸找她時,被人開槍擊斃。好了,早上八點有一班特快車,你可以搭那班來,然後...」
一聽到發生兇殺案,年輕女孩倏地站起,話筒由手中滑落。她嘆著氣,欲言又止,全身顫抖,根本站不穩,很快又跌坐在沙發扶手上。
哈吾爾.阿維納立刻生氣地對貝舒大吼:「你這笨蛋!不能換個方式講事情嗎?這下可好,看你做得好事,大笨蛋!」
他隨即掛斷電話,趕到女子身邊,扶她躺在沙發上,還拿嗅鹽硬貼著她鼻子要她聞。
「小姐,好點了嗎?雖然貝舒提到您失蹤的事,但用不著把他的話放心上,再說,您聽過他名號,應該知道這人很兩光。請您先冷靜下來,我們再一起弄清楚狀況好嗎?」
不過,哈吾爾很快就發現在這當頭實在無法釐清情況,年輕女孩身上顯然發生過什麼,令她慌亂恐懼,這部份哈吾爾還沒弄懂,她又在無預警中,聽到貝舒冒失的談話,現在她根本無法平復情緒。
他盤算了一會兒,想好該怎麼做後,便走到鏡子前,拿出用來易容改裝的化學藥劑,快速打理了自己的頭髮及面容,接著來到隔壁房間,換好衣服,再從壁櫥取出一只總是備妥的行李箱。他走出家門,直奔車庫。
哈吾爾很快開車回到家門口,他上樓重回書房。年輕女孩差不多清醒了,但表情依舊茫然,無力自行走動。哈吾爾帶著女孩來到車旁,對方並未抵抗,哈吾爾扶她上車後,盡可能讓她舒適地斜躺著。
他俯身貼近女子,在她耳邊輕聲說:「照貝舒所言,失蹤的女孩是您吧?您也住哈迪卡提爾?」
「是的,我住那兒。」
「那我們就去哈迪卡提爾吧!」
女孩看起來憂心忡忡,哈吾爾能感覺到她全身顫抖,於是他低聲勸慰,在溫柔的語氣下,女子終於卸除心防,開始流淚啜泣。
從巴黎到諾曼地的哈迪卡提爾市中心大約一百八十公里,哈吾爾開了三小時才到,途中兩人並無交談。年輕女孩已停止哭泣,沈沈睡去,隨著車行搖晃,女孩的頭偶爾會靠在哈吾爾肩上,他總會輕柔地將其扶正。女子額頭滾燙,時而發出幾聲呢喃,但哈吾爾聽不清楚內容。
天快亮了,他們來到一間小巧的教堂對面,教堂座落在蓊鬱青草中,剛好位於狹窄的河谷下方,沿著河谷往上,則會通往諾曼地科區的山嶺懸崖。教堂旁邊有條蜿蜒的小溪,往塞納河的方向流去。教堂後方有一大片草原,底下就是環繞傑羅姆港的大河。此時,天邊雲彩細薄,教堂的雕花窗櫺越發紅豔,旭日即將東昇。
整座村子尚在睡夢中,路上沒半個人影,十分安靜。
「府上離這兒不遠吧?」哈吾爾問道。
「很近,就在那裡,對面。」
他從女子指的方向望去,發現小溪邊有條清幽小徑,周圍種了四排老橡樹,小徑盡頭有一排鐵柵欄,透過柵欄即能看到一座不算大的莊園。莊園四周挖鑿了類似護城河的溝渠,並用鐵條區隔,小溪在柵欄前轉了彎,從路中央的分隔土堤下方流過,接著注入溝渠之內,並沿著渠道而流,順勢包圍砌著紅磚牆垛的高大石牆。
此情此景讓年輕女孩重新陷入恐慌,哈吾爾猜想她大概寧願逃走,也不想回到這令人擔驚受怕的地方。然而,她倒是沒有失控。
「最好別讓人看見我回來了。」她開口,「這附近有道矮門,我有鑰匙,從那兒走,不會有人知道。」
「您能自己走嗎?」哈吾爾問。
「可以的,只有一點兒路程。」
「今早天氣還算舒爽宜人,您不會冷吧?」
「不會。」
馬路中央的分隔土堤右邊岔出一條小路,恰巧橫越溝渠盡頭,小路兩側分別是高牆及果園。哈吾爾牽起年輕女孩的手臂,陪她走過小路,她看起來累壞了。
到了矮門前,哈吾爾說:「我想再逼問您也沒用,只會害您更加疲累,反正貝舒會告訴我詳情,況且,我們還會再見面的。但仍得問您一個問題,是貝舒把我房間鑰匙交給您的嗎?」
「可以說是,也可以說不是。他常提起您,所以我知道他把鑰匙放在臥室的掛鐘底下,我是幾天前偷偷拿走鑰匙的。」
「把鑰匙給我好嗎?我會在他不知情下,將鑰匙放回原處。另外,別讓任何人,包括貝舒,知道您去過巴黎,還有我載您回來的事,甚至連我們相識都別說。」
「不會有人知道的。」
「還有一件事,你我素未謀面,如今卻因某些事件意外相逢,說來也是有緣,既然您找我幫忙,我也要拜託您,請您聽從我的意見,千萬別擅自行動,能答應我嗎?」
「好的。」
「既然如此,麻煩您在這張紙上簽個名。」
哈吾爾從皮夾裡取出一張白紙,拿筆在上頭寫著:「本人全權委託哈吾爾.阿維納先生調查真相,且得以在符合本人權益前提下,做出適當決定。」
女孩欣然簽署。
「很好,」哈吾爾,「我一定會保護您的。」
他又看了一下簽名。
「凱特琳…您叫凱特琳嗎?真不錯,這名字我喜歡,先說再見,您好好休息吧!」
|